小议中国精神卫生
——翻译“Becker, A. E., & Kleinman, A. (2013). Mentalhealth and the global agenda. New EnglandJournal of Medicine, 369(1), 66-73”后记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精神卫生的发展和现状。和全球精神卫生的发展类似,中国的精神卫生也有长足的进步,但前路仍然漫漫:
1985年,《精神卫生法》开始启动立法进程;
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为精神卫生(Nations for Mental Health)”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要改善精神卫生状况;
2000年,中国开始开展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宣传活动;
2002年,卫生部等部门制定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
2003年,SARS爆发,为公共卫生,以及精神卫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机遇;
2004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启动经费为686万元的“686项目”启动了;
2009年,在新医改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12年,《精神卫生法》通过;
2014年,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已登记438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2015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出台。
当然,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发展成就并不仅仅限于以上罗列的这些事件。本文也无意对此进行详细梳理。笔者想针对Becker和Kleinman在文中谈到的问题和倡议,讨论部分中国和现状。
和全球的情况类似,中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与疾病负担的研究已足以表明精神障碍是人群健康的重大威胁。21世纪初,费立鹏的研究团队在甘肃、青海、山东、浙江四省进行了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调查。这是目前已发表的中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质量较高的成果。2012年中国还启动了全国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和疾病负担研究,负责牵头的是北大六院。同年,北京安定医院还牵头启动了新中国以来首次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调查,这将填补中国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领域的知识空白。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还将会有更多质量较高的精神障碍流行学和疾病负担研究为公众所知。
Becker和Kleinman在文中提到,全球精神卫生最大的困境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这种现状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一项结构性的因素是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极度短缺。中国的状况也是如此。《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对于现状的概括是基本准确的:“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现、随访、管理工作仍不到位,监护责任难以落实,部分贫困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依法被决定强制医疗和有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收治困难。公众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认知率低,社会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讳疾忌医多,科学就诊少。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及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
《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出台于2015年,在此前的十年中,中国已经为突破这一困境进行了重要的试验。这个试验是从“686项目”开始的。当前,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686项目”,但“686项目”这一名称所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模式,已经被基本固定下来了。一部分地区在“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相关工作,其他地区则在《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框架下进行相关工作,唯一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要求进行个案管理。各地还可能根据当地情况开展有特色的工作。根据卫计委在201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发布的消息,全国有近1/3的省份出台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专项政策,北京市、长沙市实现了门诊患者免费服药,四川对门诊患者实行定额支付且不设起付线,江西和云南对贫困家庭患者实行免费救治,湖南省将重性精神疾病救治救助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但总体来说,除了治疗费用相关政策以外,各地针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开展的管理工作都是根据之前卫生部的规定来开展的。笔者个人认为,这种模式在服务/管理对象的选取,和服务者/管理者的选择上都很有特色。
中国选择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作为突破口主要有两个考虑。一则是项目开始时经费有限,而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是整个人群中最急需帮助的:病情治疗需要只是一方面,人权侵犯是另一方面重要考量(“686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开展了相当多的“解锁”行动)。二则是吸引政府重视和资源投入的策略选择:直到现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的一大目标就是促进社会和谐,策略性地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塑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是精神卫生界的领袖为了团结综治、公安、民政等其他部门的手段。这意味着,中国的重性精神管理治疗项目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可能统一但也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照顾患者,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照顾患者的角度来说,在社区中的识别和评估,专科医生的治疗,社区中的康复都不可或缺。但目前管理项目的重点在于抓报告率和管理率。这当然也可以理解,如果要抓治疗,其可及性和有效性的评估其实是很复杂的,如果重点抓康复,那更是无从抓起,因为当前社区康复体系基本是空白。
根据目前已发表的科学文献来看,中国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仍然缺乏公共卫生意义上的评估。在之前对“686项目”的评估中,主要的结局指标是公安系统提供的肇事肇祸率,而不是健康相关的结局指标。这和“686项目”的性质有关,有相关负责人曾告知笔者,“686项目”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评估。这意味着,要评估该项目的效果,在研究设计上是困难的。另外,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中,虽然在官方的数据库中已经登记了超过400万条患者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只在卫生、综治、公安等系统之间共享,不对研究者开放,而其准确性则是另一个问题。因而,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1)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目对于病案的筛查灵敏度特异度到底怎么样?(项目中是否有非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有多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被漏掉了?)2)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目是否改善了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3)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项目的服务质量如何?4)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之中,患者的症状是否得到改善,各种健康结局是否有所提升?据笔者所知,现有一些研究团队正在就以上部分问题进行研究,期待在不久之后,相关的研究成果应该可以向公众公布。
而在谁来提供服务这个问题上,中国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确是一个创新。正如Becker和Kleinman在文中提到,中低收入国家应该让稀缺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士更多从事指导监督和培训的工作,同时应当发动初级保健医生和社区卫生工作者来进行病案的识别和管理。而“686项目”在开始阶段的确是这样做的。各地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城市和农村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架构来开展相应的工作。
但是,要全面弥合精神卫生服务的差距,提升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还需要考虑将精神卫生整合到初级保健之中。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整合与合作?Becker和Kleinman在文中并没有对此展开讨论。但各国对于将精神卫生服务整合到初级保健之中已有许多共识。首先,大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常见精神障碍(如焦虑障碍等)的患者最经常求诊的场所并不是精神卫生专科机构,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一类患者最可能出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综合性医院。多年以来大量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综合性医院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患有常见精神障碍。另外,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躯体疾病在精神专业医院往往得不到救治。考虑到中国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严重歧视,以及中国根本没有转诊体系这一事实,在综合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精神卫生专科机构之间要进行转诊是相当困难的,更不要提针对每个患者综合、连续、衔接妥当的理想状态了。
现有的《精神卫生法》和《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都显示,精神科专科医生是精神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应该是出于保证精神卫生服务质量的考虑,毕竟即便是当前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其接受的训练和服务质量也可能差异很大。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要满足中国全国人民的精神卫生需求,将成为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各地县医院正在建设精神科,但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区根本没有精神科医生。尤其当我们以慢性病管理的视角去看待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精神专科医生不可能承担常见精神障碍的全部管理人物,这就好比说,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不可能承担起全国高血压糖尿病的管理任务一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精神卫生界的共识(至少在纸面上)是要建构以社区基础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但在现实中,专科医院的扩张冲动却是难以遏制的,国家对专科医院的倾斜投入也是事实。在这种条件下,合作或者整合式的精神卫生服务可能很难进行。
此外,中国的精神卫生政策选择以重性精神疾病为突破口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相关的决策者其实也意识到这一选择可能不会缓解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歧视。每一个精神卫生领域的工作者和研究者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歧视。作为个人,选择这个领域作为研究领域都可能被身边的人阻拦。但作为研究者和卫生工作者,我们最多也就是感觉不快而已。但对于患者而言,这种歧视的后果则可能要严重得多。笔者多年前在一家综合性医院临床实习的时候,一次跟着心内科的医生去急诊会诊,送来的一个中年男性是典型的心肌梗塞,当时医院心导管手术室已被占用 ,所以优先考虑的是溶栓。当时患者的家属自称是患者的姐夫,并称患者曾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过院,暗示不用考虑患者本人的意见,并表示愿意签字放弃溶栓。不知道后来患者的结局如何,但总之是没有再送到心内科来。
这些年来,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前路依然很漫长。很多问题都值得更多讨论,比如心理治疗的地位和作用,比如物质成瘾领域的问题(针对物质成瘾的服务也应该纳入到初级保健中) ,比如老龄化背景下的精神卫生问题等等。但这也许并不是精神卫生系统内部,或者说精神医学界,可以独力处理的问题。精神卫生领域进一步的改善,可能需要依赖于整个卫生系统对于初级保健的投入,对于全科以及各种专科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在其他方面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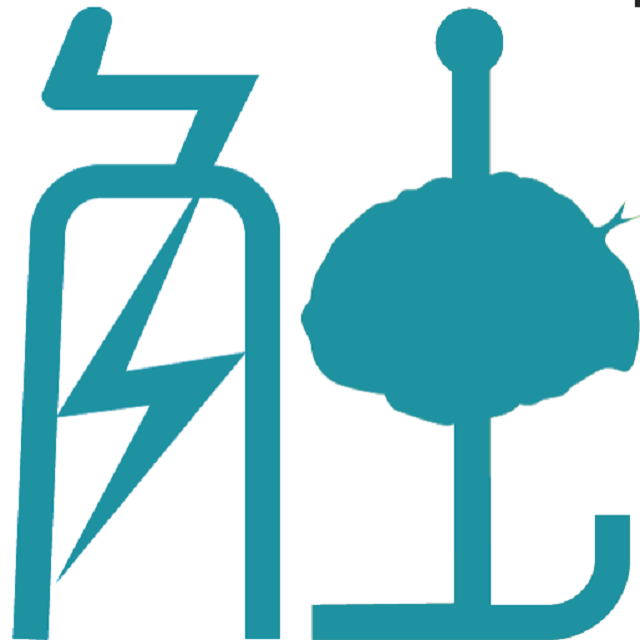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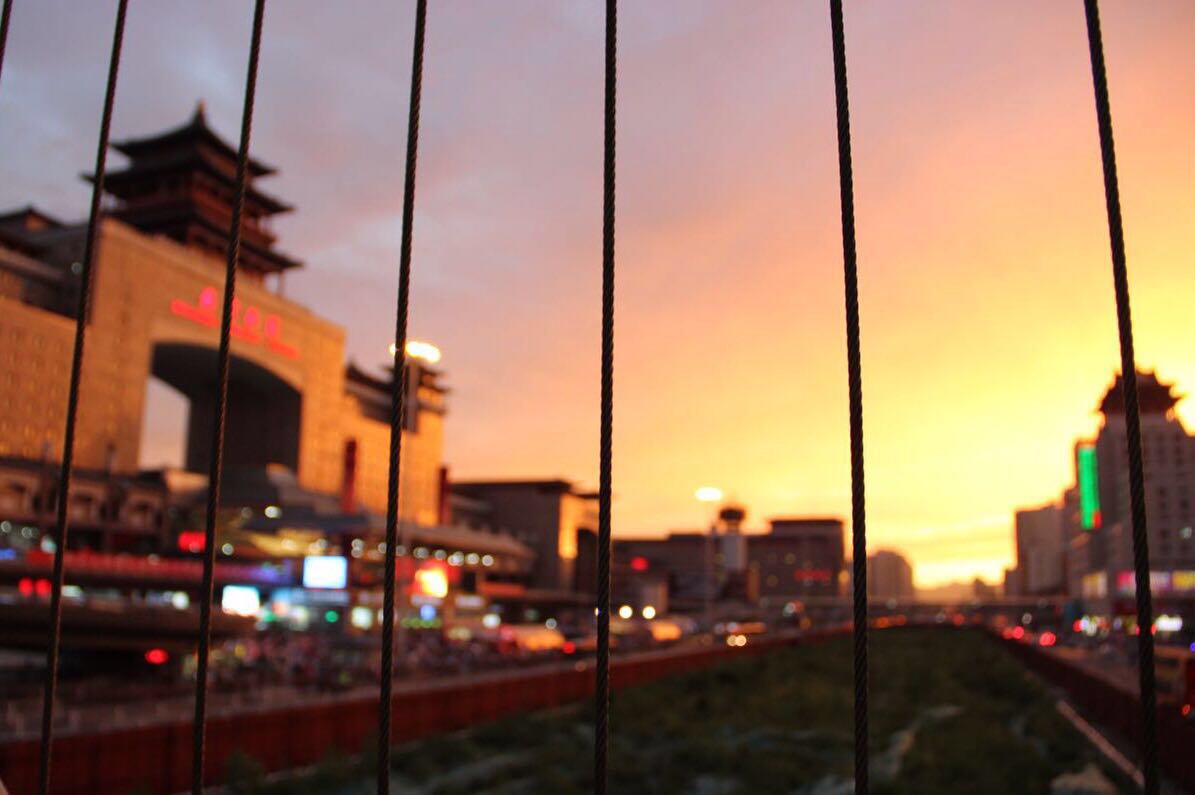



编辑您好,不知这篇述评作者是谁,站在公共卫生角度写的很到位,有深度也有前瞻性,求作者全名
您好!方便的话您发一封邮件给hi@tuchu.org,介绍一下您自己?然后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后和您联系。
除了求助,还要学会自助。自爱,爱人,尝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接受属于自己的磨难。人生不是直线,波浪起伏,既要喜欢高峰,也要接受低谷,没有坎坷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