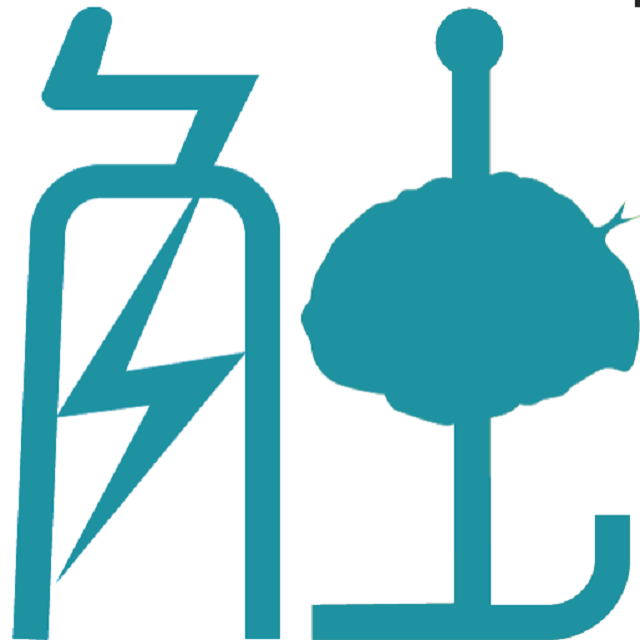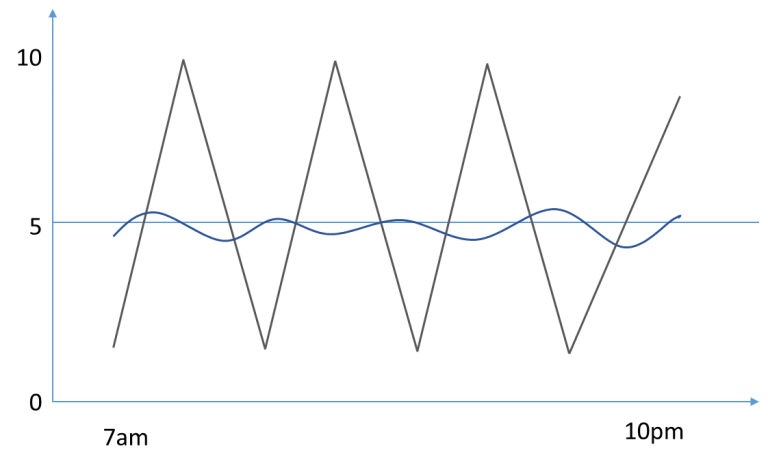村子里的酒鬼们
我有个好朋友A,她父亲是个酒鬼。从年轻时候便开始喝酒,原来只是朋友相聚喝一喝,逐渐三餐之前先喝一两二锅头,二两二锅头,到喝酒多过吃饭,到只喝酒不吃饭,到喝垮了身体;小时候A家里算小康,逐渐因为酒而争吵,哭声、打砸声,身心俱穷了下去;父亲不时因为酒后驾驶摩托车而出事故,原本一家算幸福的四口,A的愿望却是逃离这个家,母亲出走,哥哥毕业后再未回过家。三十年过去。如今一家人散开了去。A说,有时给她父亲打电话,听到那头醉醺醺的声音,也没有什么感觉了,默默就挂了。
我和A是同村的小伙伴,一起玩到大。大学也在一个城市。A对我说:“我爸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没有别的,全是酒精。”酒,在A的生活里,没有文学作品中的豪放与诗意,全是烂摊子和创伤。
在来北京读研之前,我都不知道喝酒也算个病。我只知道A的父亲不正常,但除了一起吐吐槽,安慰安慰朋友,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家所在的村子不到150人,除了A的父亲,还有其他三两个酒鬼,经常是酒鬼见酒鬼,眉开眼笑不醉不归。我们小孩子见了他们也是离得远远的。怕对方发酒疯。
在临床心理科待了半年,第一次知道了“酒精使用障碍”“酒精依赖综合征”“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酒精戒断状态”等等诊断名词。我们称他们为“酒依赖患者”。来来往往的酒依赖患者,有反复复饮N进宫的,也有真的成功戒了酒,从此回归正常生活。
某一天主任查房,一个主动来住院要求戒酒的患者说,“我在这里可以做到不喝,但回到单位,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不喝酒,工作就干不了,朋友也处不了。可是如果做不到滴酒不沾,下一次很快我就会再次住院。这次住院也是和单位说去三院看肝脏,不敢说是来六院戒酒。”
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都是借口,哼!
一个月之后我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婚礼。婚宴上觥筹交错自不必说,家宴上杯光盏影,那劝酒的架势,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对于酒依赖患者出院后“滴酒不沾”的艰巨性。酒是关系,酒是感情,酒甚至是亲情。这“酒文化”有着千年底蕴,简直坚如磐石、固若金汤。说起来好笑,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祈祷在座的各位没有酒依赖问题,没有曾经戒酒过的。否则,一杯下去,万劫不复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2001年的流行病学调查(五个城市)表明,男性、女性和总的酒依赖时点患病率分别为6.6%、0.2%和3.8%。(《精神病学》本科教材 第7版)。农村的情况如何呢?我用我直观的感觉来简单计算一下:我印象中,几乎每个村里都有3、4个酒鬼,取3个好了。我家乡的县城有20.36万人(2012年),假设患病率为1%好了,那就有2036个酒鬼。(脑补一下画面感,好可怕!)这么算也不客观。县城一共有141个自然村,按我的印象,一村3酒鬼,一共有423个酒鬼。也不少,能坐满一个电影院。
去年我回家,看到新盖的县医院大楼。进去溜达的时候看到门诊有精神心理科的诊室,惊喜了一下,屁颠屁颠跑去看。一个医生说,精神心理科只有周四下午半天的门诊,由市里的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过来坐诊。
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423个酒鬼,一个精神科医生。而这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半天还不仅仅是管酒鬼的,还要管其他精神科的疾病。我甚至有点好奇,这半天门诊有几个患者来看?即使是县城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精神疾病这个名词。
那些因酒依赖而残破凋零的人生与家庭,那些因酒依赖而满载创伤的童年阴影,那些因酒依赖而出事故死亡的人们啊,你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另一个视角:我姐姐常年在世界游荡,评论道:在菲律宾的三年,华人社团非常活跃,但是绝大部分宴席上都是果汁和饮料。只有商会换届的时候,宴会上有酒。我们都觉得,华人在异乡,能够把这根深蒂固的“酒文化”给抛弃了也挺不容易的。
PS:给有戒酒需要的人(转自北大六院临床心理科):戒酒无名会(AA)中国网络分会。
AA完全免费、来去自由,想戒酒(或想帮家人戒酒)请参加AA的中国网络会议。
AA网络会议每晚20:00在YY频道20260719/16537750/51/43854999举行。
家属网络会每晚21:00在YY频道11935610举行。
YY客户端请在www.yy.com下载、安装、注册。
关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部分信息可以登录http://www.aa-beijing.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