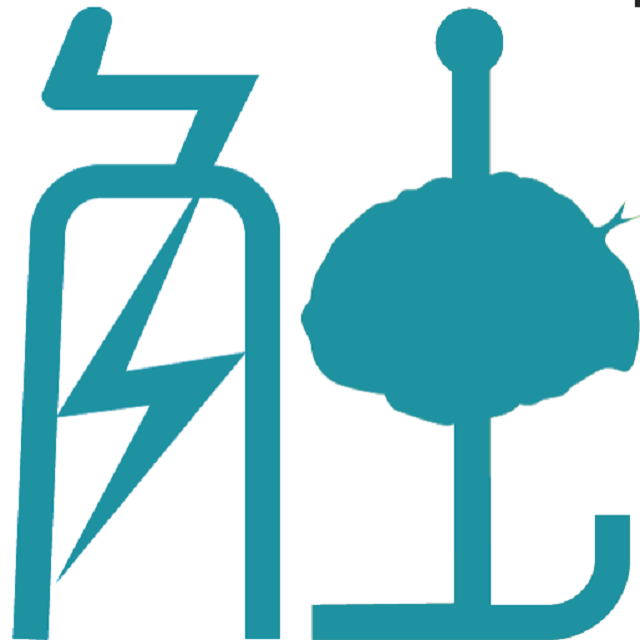那里是精神病院

文/@梁晓声
慈爱
高墙内,集中错乱的意识形态;外,是正常的,普识如是。
三排旧红砖房,分隔成若干房间。对扇铁门,仿佛从没开过。上有小门,一天也开不了几次。院中央有一棵树,塔松,栽不久。铁门左右的墙根,喇叭花在夏季里散紫翻红,是美的看点……
我父母去世后,我将从二十一岁就患了精神病的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他起初两年就在那里住院。
哥的病房,算他五名病人。二人与哥友好。一是丘师傅,比哥的年龄还大,七十几岁了;一是最年轻的病人邹良,绰号“周郎”。丘师傅曾是某饭店大厨,据老哥讲,他患病是儿女气的,而“周郎”原是汽车修配工,因失恋而精神受伤。他整天闹着要出院,像小孩盼父母接自己回家。
某日傍晚,大雨滂沱。坐在窗前发呆的丘师傅,忽然站起,神情焦虑,显然有不安的发现。于是引起其他病友注意,都向那窗口聚集过去。斯时雨鞭夹杂冰雹,积满院子的雨水已深可没踝。指甲大的冰雹,砸得水面如同沸鼎。而一只小野猫,无处可躲,境况可怜。它四爪分开,紧紧挠住塔松树干,膏药似的贴着,雷电间歇,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叫。才是不大点儿的一只小猫,估计也就出生两个多月。它那种恐惧而绝望的叫声,带足了求救意味。塔松叶密,它已无法爬得再高;全身的毛被淋透,分明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丘师傅毫无先兆地胃疼起来,扑在床上翻滚。病友们就拉开窗,齐声叫喊医护人员。一名穿水靴的护士撑伞而至,刚将门打开,丘师傅一跃而起,冲出——他从树上解救下了那只小野猫,抱在怀里跑回病房。待护士恍然大悟,小野猫已在丘师傅被里,眼前的丘师傅成了落汤鸡。护士训斥他不该那么做,命立刻将小野猫丢出去。丘师傅反斥道:“是你天使该说的话吗?”护士很无奈,嘟哝而去。从此,那一只小野猫成了那一病房里五名精神病患者集体的宠物。每当医护人员干涉,必遭一致而又强烈的抗议。
女院长倒是颇以病人为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康复,破例允许。丘师傅贡献洗脚盆当小猫沙盆,于是以后洗脸盆一盆二用。而“周郎”,则主动承担起了清理沙盆的责任。院长怕院子里有难闻气味,要求必须将猫沙深埋。都是来自底层人家的病人,谁又出得起钱为小猫买什么真正的猫沙呢?每日在院子里做过集体操后,同病房的五人,这里那里铲起土,用扇破纱窗筛细,再用塑料袋带回病房。他们并没给小野猫起名,都叫它“咪咪”而已。当明白了它是一只瞎眼的小野猫,更怜爱之。
“咪咪”肯定是一只长毛野猫和短毛野猫的后代,一身金黄色长毛,背有松鼠那种漂亮的黑色条纹。而脸,却是短毛猫的脸,秀气,极有立体感。倘蹲踞着,令人联想到刚走下T台的模特,裹裘皮大衣小憩,准备随时起身再次亮相。“咪咪”特文静,丘师傅枕旁的一角,是它最常卧着的地方。而且,一向紧靠床边。似乎它能意识到,一只侥幸被人收养的流浪猫,有一处最安全的地方卧着,已是福分。它很快就对病房里五个人的声音都很熟悉了,不管谁唤它,便循声过去,伏在那人旁边。且“喵喵”叫几声,表达娇怯的取悦和感恩。它极胆小,一听到医护人员开门锁的响动,就迅速溜回丘师傅的床,穿山甲似的,拱起褥子,钻入褥子底下。有次中午,另一病房的一名病人闯来,一见“咪咪”,大呼小叫,扑之逮之,使“咪咪”受到空前惊吓。“周郎”生气,厉色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咪咪”的惊恐却未随之清除,还是经常往褥子底下钻。五名精神病人困惑,留意观察,终于晓得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病房走动时,脚下塑料拖鞋发出的“咯吱”声。拖鞋是医院统一发的,“咪咪”难以从声音判断,是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又来了?他们便将五双拖鞋退了,凑钱让护士给买了五双胶底的软拖鞋。此事,在医护人员中传为精神病患者们的逸事…
那是一家民办的康复型精神病院,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住院费较低,每月一千余元。亲人拿患者实在没办法了,只得送这里来接受一时的“托管”。病情稍一好转,便接回家去。每月一千余元,对百姓人家那也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啊!所以,病员流动性大。两个月后,同病房的病友已换二人;两名新病人不喜欢猫……
丘师傅对“周郎”比以往更友好了,有时甚至显出巴结的意思。他将自己的东西,一次一两件慷慨地给予“周郎”。当他连挺高级的电动剃须刀也给予时,他最年轻的病友惴惴不安了。当着我老哥的面,“周郎”问: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丘师傅却说:“近来,我夜里总喘不上气儿。”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觉得,我活不长了。”
“我的东西,有你看得上眼的吗?”
“你说,我要是死了,咪咪怎么办?”
“还有我和老梁爱护它呀。”
“老梁是指望不上的。他弟弟不是每次来都说,正替他联系别的医院吗?”
“就是老梁转院了,那还剩我呢!”
“你要是出院了呢?” .
“那我就不出院。不行,我家穷,我也不能总住院啊!”
“我要是真死了,会留给医院一笔钱,作为你的住院费。为了咪咪,你可要能住多久住多久,行不?”
“这行,哎你还有什么东西给我?”
“我死了,我的一切东西,凡你想要的都归你……”
我去探视哥哥时,哥哥将他的两名病友的话讲给我听,显出嫉妒友情的样子。我笑笑,当耳旁风。
翌年中秋节前,我买了几箱水果又去,听一名护士告诉我,丘师傅死了。患者来去,物是人非。认得我并且我也认得的,寥寥无几了。
在探视室,我意外地见到了“周郎”,他膝上安静地卧着咪咪。那猫长大了,出落得越发漂亮。他老父母,坐他对面。
“儿呀,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他老母亲劝他。看来,已劝很久。
“周郎”说:“爸,妈,我的病还没轻我不回家。”
他老父亲急了,训道:“你就是因为这只猫!”
“还因为丘师傅,他活着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我们对你就不好了吗?”
“爸,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得说话算话啊!”
那是精神病人的青年,轻抚了几下咪咪,突然长啸:“啊哈!我乃周瑜是也……”
接着,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唱京剧。而咪咪,动一动,更加舒服地卧他膝上,习以为常。
两位老人,眼中就都流泪。
我的哥哥患病四十余年中,我无数次出入各类精神病院,见过各种表现的许许多多的精神病人;却第一次听到精神病人不肯出院的话,为一只瞎猫,一份承诺,和对友情的感激……
我心怦然。
我心愀然。
“周郎”终于不唱,指着我对老父母说:“你们问问这个是作家的人,我一走了之,那对吗?” .
两位老人,也都泪眼模糊地看我,意思是——我们的儿子,他究竟说的是明白话还是糊涂话啊?
我将两位老人请到探视室外,安慰他们:既然他们的儿子不肯出院,又何必非接他出院不可呢?随他,不是少操心吗?
两位老人说,一想到住院费是别人预付的,过意不去。
这时院长走来,说丘师傅根本没留下什么钱。说丘师傅自己的住院费还欠着一个多月的,儿女们拖赖着不肯来交。又说小周是几进几出的老患者了,医院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轻患者,老患者,利于带动其他患者配合治疗。民政部门对院方有要求,照顾某些贫困家庭是要求之一。并大大夸奖了“周郎”一番,说他守纪律,爱劳动,善于团结病友。
我扭头向病室看时,见“周郎”在室内侧耳聆听……
如今,六七年过去了,我的哥哥,早就转到现在这一所医院了。
几天前我去探视他,陪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陪他吃水果,聊天。
老哥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小周吗?就是我在前一所医院的病友……”
我说记得。
哥哥又说:“他总算熬到出院的一天了。”
我惊讶:“他刚出院?你怎么知道?”
“我们一直通信来着。”
“你和他?……一直通信?……” .
“咪咪病死了。小周把它埋在了那一棵松树下。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做了一回说话算话的人,感觉极好……”
“怎么好法?”
“那他没说。”
六月的夕阳,将温暖的阳光,无偿地照在我和我的老哥哥的身上。四周静谧,有丁香的香气。
我说:“把小周写给你的信,全给我看看。”
哥说:“不给你看。小周嘱咐,不给任何人看。”
老哥哥缓缓地享受地吸烟,微蹙眉头,想着一个老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的某些错乱的问题。四十余年来,他居然从不觉得思想着是累的。
我默默地看他,想着我们精神正常的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已使我们思想得厌倦。
忽然他问:“哪天接我出院?”
那是世上一切精神病人的经典话语。
他眼中闪耀渴望的光……
斯文
那里,我所见到的最斯文的人,莫过于第六病房的“二十八床”。
哥哥也在第六病房。哥哥的床位是二十七。
有次我进入第六病房为哥哥换被罩、换褥单,并要将他的脏衣服带走,于是看到了哥哥那名最斯文的病友。我说他最斯文,乃与别的患者相对而言,也是指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当时他的床上放着笔记本电脑,看起来那电脑还是新的。他正背对着哥哥的二十七床打字。我是一个超笨的人,至今不会操作电脑,故对能熟练操作电脑的人,每心生大的羡慕。他背对着哥哥的床,便是面对着病房的门。患者们都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没用哥哥陪我进病房,而是自己进入的。我以为六病房那会儿没人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猛可地见一个人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用笔记本电脑打字,别提令我多么惊讶了。
他四十几岁的样子,脸形瘦削,白皙,颜面保养得很好。显然是个无须男子,脸上未有接触过剃须刀的迹象。那么一种脸的男子,年轻时定是奶油小生无疑。连他的脸,也给我斯文的印象。那时已是初秋月份,他上穿一件灰色西服,西服内是白色衬衣。衬衣的领子很挺,尚未洗过。而且,系着领带;暗红色的,有黑条纹。他理过发没几天,对于中年男子,那是发型最精神的时候。他的头发挺黑,分明经常焗染;右分式,梳得极贴顺,梳齿痕明显,固定,因为喷了发胶的缘故。有些男子对自己的发型是特别在乎的,喜欢要那么一种刻意为之的效果。看来他属于那一类男子。
我以为自己进错了地方,撤回已经进入病房的那一只脚,抬头看门上方的号牌——没错,这才步子轻轻地走入。
他抬头看我一眼,目光随即又落在电脑屏幕上。我经过他身旁时,瞥见一双比他的脸更白皙的手。那是一双指甲修剪得很仔细的手,数指并用,在键盘上飞快的敲点,如同钢琴家在微型钢琴上弹奏一支胸有成竹的曲子。
我走到哥的病床旁,于是也就站在了他背后。他立刻将电脑合上,却没合严,用几根手指卡着。分明的,防止我偷看。
这使我觉得不自在。
我低声地,也是很礼貌地问:“我想为我哥哥换被罩和床单,可以吗?”
“请便。”
他的语调听来蛮客气的,并无拒人千里的意味儿。但是,一动未动。
我开始做我要做的事,他站起来,捧起电脑。我发现他下身穿的却只不过是病服裤子,脚上是医院发的那种廉价的硬塑料鞋。袜子却肯定是他自己的。一双雪白的布袜。
我于是断定,这个起初使我另眼相看的男子,终究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在我看着他的背发愣之际,他转过了身,彬彬有礼地说:“让您见笑了!”
之后,捧着电脑绕到他病床的另一侧,再将小凳也拎过去,款款坐下,又打起字来。那么,我就是有一米长的脖子,也难以偷看到他在打些什么内容了。
再之后,彼此无语,我默默做我的事,偶尔瞥他一眼,见他嘴角浮现笑意。是冷笑。一丝。
冷笑……
还是冷笑……
我于是感觉周身发寒。
在一阵阵或急促或徐缓的敲键声中,我终于做完了我的事。
当我离开病房时,他头也不抬地说:“再见。”
连他的语调,也变得冷冰冰的了……
来到院子里,我问哥哥,他病房那名新病友起先是什么人?
老哥说,“二十八床”是外地来的,在一座小城里当过科长,至于哪方面的科长,老哥也不清楚。 我说,在小城,科长是挺有权的人了。精神病,那也不一定非要到北京才能治啊。
老哥说,那小城没精神病院。“二十八床”已在省城的精神病住过两次院了,未见好转……
我和院长熟了,遂怀着困惑去问院长。
院长告诉我:“二十八床”原本当科长当的挺舒服的。那是小城里的闲职,属于权虚事少,却又非有不可的位置。在从前,那类科长的班上情形,被形容为吸着烟,饮着茶,看着报,接电话,发文件。现而今,办公现代化了,配电脑了,于是连报也不看了,变成拿公务员工资的“网虫”了。起初还只不过在办公室里玩玩网上麻将或电脑游戏,后来腻歪了,兴趣转向热衷于参与网上话题了。一坐办公椅上,第一件事便是开电脑,接着一通点击搜索。有讨论可参与,便激动,便亢奋。倘无,一天都没精神,缺氧似的。偏偏那一时期,要提拔一位副处长。他已做了八九年科长,自认为早该轮到提拔他了。属下们也有这种看法,甚至预先对他说恭喜的话了。他呢,半情愿不情愿的,已宴请过两次了。不料竟是梦里看花水中捞月一场空,他是多么的郁闷和失落不言而喻。大约从那时起,他开始在网上骂人了。他骂人并非由于观点对立,仅仅是需要骂人。用日语说,是“无差别之骂”,随意性极大。闯入一个网站,只要有话题,上来就是一通乱骂。也许在这个网站似乎支持甲方,大骂乙方。到了下一网站,同一话题,挨他骂的却是乙方了。日复一日,越骂越花花,越骂越来劲儿。最后,也在各机关网站开骂了,而且专骂熟人,朋友也不例外,骂得最具快感。骂过之后,见了面照旧握手、拍肩、称兄道弟,亲热有加。快感也有加。却又心里犯嘀咕,怕熟人和朋友们有朝一日识破他的两面性,于是加倍地对熟人和朋友主动示好。那么做了,心理不平衡,背地里又在网上骂,于是活得心里超累。某日,同事们在办公室谈网络之事,讲到了与他类似之人的类似之事,他就以为是含沙射影,针对他;大打出手,接着歇斯底里大发作。其实同事们根本不是在说他,是他自我暴露了。若不然,挨过他骂的人谁都不会想到骂自己的是他。北京的正式精神病院,经过会诊,宣布他为最严重精神分裂型患者。也就是说,基本没治了。他的家人听说这里是托管型的精神病医院,通过关系将他送来,但求眼不见心不烦……
“那,还让他接触电脑?”
“不让不行啊,戒毒还得有个过程嘛,再说那电脑是台废的,外壳新。除了打字的功能,其它功能一概不具备。”
“他不知道?”
“他也和那台电脑一样,其它认知能力迅速退化了。只要还能通过电脑这一载体敲出一行行骂人的字来,他的病情暂时就不会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唉,原来不错的一个人,可惜了!”
我亦叹道:“都是网络惹的祸。”
院长立刻反驳:“你这种说法我绝不苟同。不是网络使他成了精神病人,而是网络使他的精神分裂潜伏期延长了。没有网络,他早该疯了,还不知会以多么暴烈的方式发作呢!”
我说:“难道他的亲人们还得替他感谢网络?”
不料院长说出一句话竟是:“连我们中国都得感谢网络!”
我一怔,表示愿听端详。
院长接着说:“你想过没有,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啊!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任何一类群体,都将是世界上最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使人浮躁,使人倦怠,使人郁闷,使人怨毒,使人心理紧张,使人生理紊乱,使人人格分裂,使人找不到北,使人想骂人,使人产生攻击的冲动。如果能够统计,为数肯定不小。幸亏有网络,使这样的人们有减压的途径。当然网络带给人类的其它好处很多,很巨大。比如推动民主,促进法制,监督腐败。但我指出的,也是一大好处。当然减压的方式很多,许多方式健康、优雅。但没有经济条件优雅,也感觉压力重重,也希望减压的人们,他们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减压,同志,可以理解的吧?……”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离开精神病院,我的心情特复杂。觉得受益匪浅,亦觉得被歪理邪说所蛊,认识混乱,也有点找不到北了。
过马路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险些撞着我。
我心头攸恼,正想骂他一句,却被对象抢先了。
“你他妈瞎呀?!”
对方扬长而去。
回到家里,我命儿子替我开了电脑,打算在我的博客上大骂那骑自行车的人;一想,自己不会打字,身为父亲,口言骂人话,命儿子敲在电脑上,这等事我还是做不出来。
于是只在心里骂了一句:“你他妈才瞎了呢!”
快感。小的。
却毕竟,是快感……
分裂
还是那里。
我又去探视哥哥时,恰逢全体病人(男子病人区)刚在院子里做完操。他们还有半点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在这半点钟里,想吸烟的可以吸。而烟,是他们集合在院子里了才发给的。不吸烟的,也不愿提前回病房。这儿那儿,蹲一起发呆。有的,无缘由地笑。还有的,双手抱头,陷于正常人不解的苦恼。
那会儿,他们与高墙外的人们的不同,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那会儿,看到他们的人会不由得庆幸,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那会儿,我陪我的哥哥在探视室聊天。
我忽然觉得院子里骚乱了,起身走到窗前朝院子里望,见一名歇斯底里发作的患者在抢别人正吸着的烟。有人将烟背到身后,佯装并没吸烟的样子。有人躲远偷偷吸。有一个人反应慢了点,结果叼在嘴上的烟被抢去。然而抢烟的患者并没吸成,烟烫了他的手,掉地上了。
“看你,不好言好语地要,偏动抢,烫手了吧?”
身体高大强壮的患者,语调温良地说着,将很短的一截烟蒂踩灭。
瘦小的患者,于是低声下气地乞求:“给我一支烟!”
高大强壮的患者却说:“我不能给你烟。医生护士都不允许。你因为吸烟,夜里咳嗽成什么样你自己忘了吗?再吸,又得为你输液了。输一次液得花不少钱,你家里那么困难,你怎么就不为你家里人想一想?……”
啪——他的话还没说完,挨了一记耳光。
我觉得问题严峻了,跨出探视室,打算以正常人的角色制止难以想象的事态。
但出乎我的预料的是,高大强壮的患者,却并未立即向瘦小的患者发威。他摸了一下脸颊,竟笑了,依然用温良的语调说:“好心好意劝你,你反而打我,你对呀?”
那时,在我看来,高大强壮的患者,简直绅士极了,斯文极了。
“你他妈给我一支烟!”
瘦小的患者还要打,高大强壮的患者没有躲。
瘦小的患者讨不到烟,也打不到人,于是辱骂。其言污秽,不堪入耳。
“那么脏的话,你怎么骂得出口啊!”
高大强壮的患者,脸红到了脖子,他一转身提前回病房去了……
瘦小的患者达不到目的,四下睃寻,又抢别人的烟,向别人讨;抢不到也讨不到,打别人,骂别人……
被打者,竟无一人还手。
被骂者,也都像那高大强壮的患者一样,默默躲入病房。
“别跟他一般见识!”
“都让着他点儿!”
“他属于重病号!”
“他初来乍到,带进来了外边……“
我听到有的患者在互相告诫。
那一时刻,在我看来,满院的精神病患者,除了瘦小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那一个,皆绅士极了,斯文极了,有涵养极了;与我在高墙外的世界每见每闻的情形完全相反……
我愕然。
我困惑。
一位医生两名护士出现了。
“三床的,你又胡闹!丢不丢人啊?”
瘦小的患者,顿时变乖了……
我忍不住与医生交谈,虔诚地向他请教,为什么那些个精神病患者,在刚才那么一种情况之下,其表现居然都那么的良好?是不是给他们服用了某种进口的,特效的新药?
医生笑了,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一种高级的药研制出来。
他耐心向我解释,其实是精神病院这一种特殊的环境,对精神病患者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种病,只要患者在家里服药就足以使病情稳定,减轻,却须一再接受住院治疗的原因……
见我还是不明所以,他又说——凡精神病人,在家里时,大抵都是不肯承认自己患了精神病的。因为家庭的环境,难以使患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与他的亲人们显然不同。精神病患于脑内,没有任何体表症状,亦无脏器痛苦,亲人要使患者懂得自己患了精神病,绝非易事。但精神病患者一住进精神病院,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向他传达一种信息——他患精神病了。渐渐的,他们也就能够接受这一现实,面对这一现实了。而这是精神病学的心理学前提。一个人,当他承认自己患了精神病,那么也就等于他同时明白了——如果他想离开医院,他就一定要使自己的表现不异于精神正常的人。他也明白,只有当他变得那样以后,他才被认为病情治愈了,起码是减轻了。怎样的人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呢?对于男人而言,正如你刚才所见,在某种情况之下,要尽量表现得有绅士风度、斯文、有涵养。一句话,轻型精神病人,或由重转轻的精神病人,他们做人是很有目标的……
医生问我:“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一篇文章中,怎么评价白求恩来着的?”
我回答:“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医生说:“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以这三条来形容某些精神病人的做人目标,那也是比较恰当的……只不过……”
他沉吟片刻,也向我请教:“什么样的人,才算一个纯粹的人?”
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不知道。当年曾希望搞明白,至今还是不明白。”
“也许,指表里如一吧?”
我说:“那么纯粹的人,岂非太少了?”
他说:“所以毛主席才称颂白求恩啊。”
当我离开精神病院,一路走,不禁地一路想——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差不多人人皆有目标,某些人还有诸种目标。但在做人方面有目标的,多乎哉?寡乎哉?这是精神正常的人们的无奈吧?
里边的世界很无奈,但精神病患者们,他们居然有做人的目标——如果那位精神病医生的话是值得相信的,那么可不可以说,里边的世界不无精彩呢?
我于是驻足,转身,回望那高墙,那铁门。
倏忽间我心生恐慌——自己如此胡思乱想,难道也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了?……
突触君:本文原载《海燕》2008年第10期,真的是非常温暖的故事。作为一只每天呆在精神病院的准医生,所接触到的虽与文中描绘的不尽相同(如在我们医院,患者是不允许带电脑的,另外医院条件要比文中好很多),但是内心是和作者共鸣的。精神病人并不可怕,多一点关注,多一点温暖。